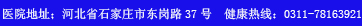一叶轻舟下婺江潇湘晨报
2023/5/17 来源:不详北京手足癣医院那里好 http://m.39.net/baidianfeng/a_8833423.html
金华新闻客户端9月21日消息通讯员张苑/文徐美琴/摄
陈志清是婺江的儿子,祖祖辈辈在船上漂了数百年,在风里生,在雨里长,在变幻的云彩里看天的脸色,在与船桨的对话中摸清了水的脾性。七旬风雨人生路,婺江风云近百年。陈志清不是罗贯中笔下的白发渔樵,却是行游江渚的虔诚赤子。自儿时轻舟越江海,而立之年渔民上岸安家,直至如今九号码头最终征迁,婺江旧貌换新颜,他日日往水里去,在岸上走,在无限风光里,打捞起那些年的日出日落、江枫渔火……
岸上沧海
船上的男孩长到七、八岁,就担起了拉纤的苦差事。一叶扁舟,逆水而上,迎风而行,船上堆满了各色物产,有水里的,也有山上的。船老大在船头掌着舵,妹妹们不似歌里唱的那样坐在船头,而是被男人们护在了船尾。粗壮的纤绳仿佛千年巨蟒,绷直了身子,由船上探到岸上,爬上五、六条黝黑光滑的脊背,这一个个幼小的身躯被吃尽了力气,向前蜷曲着低下头去,犹如一只只爬行的龟。他们站稳了双腿,匍匐着向大地攫取无尽的能量,支撑起攀爬生活的脊梁。“嘿——哟,嘿——哟,嘿——哟……”他们齐声呼出船上人独特的劳动号子,这号子里是婺江儿女的倔强,也是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冲锋号。
这“嘿——哟”声渐渐大起来,穿过密集的雨、漆黑的夜,跨过悬崖沟壑、叠嶂层峦,化作一柄柄锋利的刀剑,刻画出一个个茁壮的体魄和刚强的灵魂。他们担起了更多的负重。金华码头由东向西,从一号到九号,绵延四华里,一艘艘货轮被这些身躯牵引着靠岸,由五六吨到十余吨,从五六艘到十余艘。安地来的山货、武义来的石灰、兰溪来的纺纱、蒋堂来的粮食、衢州来的木材、北山来的草药……南来北往的货轮在金华码头靠岸,依次排开,货物卸了又装,而后远航。
到了上世纪70年代,金华码头的2、3门各有了一台吊机,如两条钢铁巨龙盘踞在婺江之畔,舞动着灵活的脖颈,伸展着龙舌吞吐岸上船里的庞然大物。它们将码头上的大量人力解放了出来,也向天地讲述着一个工业时代的到来。一船船货物由水上搬到了岸上,再由三轮车装载着,一部分运到城里,更多的被存进了仅隔一条马路的货场仓库,等待着“轰隆隆”的火车汽笛声,从遥远的地方赶来,稍作喘息,又裹挟着它们飞驰而去。
水下风云
和火车一起飞驰而去的或许还有水下的世界。岸上的路越来越多,柏油马路、高速路、高架桥、铁轨……纵横捭阖。滚滚车轮在马路上轧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印记,无止尽的采沙作业也在水下挖出了密密麻麻的沟沟坎坎,浅的五、六米,深的八、九米,直挖去了千年沉积的流沙,露出了黏腻的红土,漾起一滩浑浊,攒起一处处暗藏的旋涡。
识水性的,或不识水性的人蹚水下去,游着游着突然就扑腾起来,而后三五个人抱成一团,慌乱中开始呼救。这时候,陈志清远远地望见了,丢了渔网,径直划船过去,判断缓急,能抓头发就抓头发,能拉手臂就拉手臂,能扯衣服就扯衣服,徒手将人一个个救上了船。被救上船的人有母子,有青年伙伴,有偷跑出来玩得一家五六个小娃娃……
日子久了,陈志清渐渐摸清了水下的暗流,早早地提醒下水的人别往那儿去。下水的人见风平浪静,不以为意,肆无忌惮地靠过去。陈志清划着船,远远地看,不敢出米的半径圈,看那人靠旋涡近了,就快速划过去捞人。
让陈志清印象最深刻的还是4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的夜。晚饭吃得饱,睡意昏沉,浅浅地眯着靠在床头,这是船上人的习惯。朦朦胧胧听见有人呼救,那是水里来的声音,陈志清一下清醒起来,拔腿就往外跑,妻子在后面追着给他披棉衣,步子却不及他快。他在前面撑船,妻子在后面划桨,摸黑循声找去。那人扑腾地太急,伸手下去够不着,陈志清只能光身下水去找。
几番周折,终于拖人上船,两个人都冻伤了,马上靠岸,在岸边堆柴烤火。水和火是船上人相生相克的根,他们向水讨生活,在船上生火做饭,他们借水行舟,高举火把驱散威胁和侵袭。给捞上来的那人裹上自己的棉衣,那人挨着火借着酒劲干嚎。就在那年那夜的火堆旁,陈志清望着那一江白霜,感受着自己的身子一点点回暖,一遍遍地开始怀念江河浅滩从前的模样。
义乌江、武义江交汇而成婺江,一路向西合流衢江,下兰江,入富春江,去往钱塘江,人在船上,一眼就能望见水下的路。水上的路不似岸上多,水底藏着水路的跟卖,前人摸清的路早已烙在后人的心上。船上的人在码头上支起竹栅栏,将靠岸的泥沙拦在外面,留出一个个深深的水湾,水满且平,船总能稳稳地靠岸。
一字排开的9个码头,通济桥下的水湾最深,有9米,一枚针掉下去都能看清楚。八咏楼前还有一片八咏滩,据说古时大将军就在这滩上练兵。每年夏天,甲鱼们就赶在夜里爬上滩来产卵。那时的陈志清不过八九岁,每天提着篮子捡上30斤甲鱼,拿到小码头上卖,三毛二一斤,一天能赚10块钱。码头上的早点总是很丰盛,往来货物也多,而且便宜,陈志清总会舒舒服服地吃个早饭,然后采买些水果,给兄弟姐妹们带回去,回家还能剩五块钱。
可是,早在30年前,婺江边的河滩上就没有甲鱼了。连带捕上来的鱼都有一股柴油味,不好吃,更不好卖。江里污水横流,一网撒下去,总会网上来一些垃圾,小俞逃出网,转眼就看不见踪影。
岁月浪涛
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船上人相信风水轮流转,凡事都和浪涛一样总有起起伏伏,岁月也有属于它的潮汐。
10年前,整个浙江省开始推进“五水共治”。千万人穿上红马甲,下水捞垃圾;一辆辆大卡车开进河湖库塘,开展清淤行动;星罗棋布的管网连接千家万户,实现截污纳管;河道两旁植树种草,建起了生态绿岸;政府还为每一条河流都落实了“河长制”,日日督查,月月巡河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很快,水变清了,草变绿了,滔滔婺江水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明显变化。从黑五类水到四类水、三类水、二类水,甚至是一类水,一次次的水样抽检传来婺江复活的利好。
如今的婺江,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,三江六岸,绿树映红花,彩虹桥横跨南北,夜空下游人如织话桑麻。作为钱塘诗路带的源头,婺江重启歌喉,吟咏着万古芳华。
陈志清对这样的巨变并不陌生。祖父辈在船上活了一辈子,他在船上长了30年,又在岸上住了40多年。新中国的这70年也是渔民生活变化最大的70年。
祖辈行舟打渔,风水为乡船作宅,船开到哪儿,鱼就卖到哪儿。新中国成立后,进入计划经济时代。渔民们顺流而下,顺风而行,一张网撒到石柱头,到白鸭卢,到嵊州,到千岛湖,然后依照规定坐火车回来卖给金华蔬果公司,再换了粮票布票,买米置衣,再坐火车回到船上去。
且说江头鱼米贱,红脍黄橙香稻饭,渔民的伙食从来不算太苦。那时的八咏滩旁还有个长乐剧院,一半的墙角都没在水里,渔民们得了闲,将船靠岸,还能欢欢喜喜地看场戏。夜里拴了船,躺在里面,外面是纤夫的号子声、小贩的吆喝声、锅碗瓢盆声、货物装卸声……声声入耳,独独没有读书声。不一样的码头,一样的嘈杂,一样的漂泊,却总能香甜地睡去。
改革开放的东风吹起来,吹进了渔民们的梦乡。上世纪70年代末,政府安排渔民们上岸安家,每人分到20多平方米,白天出船打渔,晚上上岸回家。船上拉货的人都安排进金华车辆厂当了工人。不是离了船不能活,船上人总有一份根深蒂固的亲水基因,陈志清把房子选在了九号码头边,看得到江,听得到码头的声响。
风云变幻40年,九号码头最终征迁,陈志清家所在的综合楼也纳入拆迁。这个和渔船打了大半辈子交到的老人又一次和过去告别,可眼前的一汪婺江水却愈发亲切起来。他时常携着妻子,领着5岁的小孙女,到江边走一走,再到船上荡悠一会儿。
自孙女辈起,孩子们都能安安稳稳地上学。每到端午,婺江上会有赛龙舟,燕尾洲也有了游船,五百滩上还有了画舫,而他的旧船上,有风云百年的江湖。
声明: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。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,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,谢谢。邮箱